

湖北省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田垄间,80岁的刘文豹种地四十余年,每次来到田间地头,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热爱。
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农民,并不一般。
除了有着老农人的勤劳质朴外,他还是个机械能手,开荒改良土地,种出几千万斤粮食,被称为一代“粮王”。

3月11日,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,在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的枣阳弘农家庭农场,80岁的刘文豹蹲在麦田里,顺手拔起一株麦苗查看长势。

“长势还可以,你给老二交代一下,注意病虫害,要备齐机械、农药,做到及时防控。”刘文豹吩咐大儿子刘斌。
“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种了一辈子粮,经验丰富。我们都听他的。”刘斌告诉记者,尽管父亲年龄大了,又有高血压,但每天转田埂是少不了的。
“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,那就是种粮,现在不仅自己种,两个儿子也跟着一起种。”谈及过往,刘文豹轻描淡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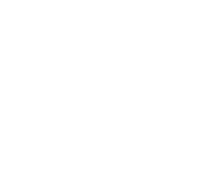
刘文豹是南漳县李庙镇人,20世纪90年代初期,他凭借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,成为当时湖北最大的种粮户,并获得了“一代粮王”的美誉。
时针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,春潮涌动,万象更新。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等待一场久旱逢甘霖般的变革。常年受困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一次生产力的极大解放。但真正敢从常年的束缚中挣脱出来,迈出那一步的人还是少数。
但历史会奖励向前一步的人。
刘文豹感受到了春风拂面的暖意,他觉得这是个大好的机会,跃跃欲试。而且他从不想太多,“干就是了。”就是这四个字,贯穿了刘文豹的一生。但凡这其中掺杂了一些利弊得失的计较,“粮王”的故事恐怕就是另一番面貌。只要做事,总会遇到失败,但就是这起落成败的跌宕起伏,反复考验和捶打着一个人的决心。

由于刘文豹之前当过国营农场的农机员,1982年他便自筹资金买了4台拖拉机,搞起了“农机代耕”。在那个家家户户还是牛犁地的年代,农机的意义不亚于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。所以那时刘文豹的生意特别好,“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,有一次连着7天7夜没睡个囫囵觉,等种完地骑自行车回家时,一头栽倒在地上睡着了。”而且他自己就是农民,处处以农民的利益为重,“绝不让农民吃亏。”就靠着这两年的辛苦与忙碌,刘文豹攒下了第一桶金。
尝到了政策甜头的刘文豹又开始琢磨,“与其只帮别人搞一个生产环节,不如承包种地的全过程。”而且他认识到,规模才能出效益,便一口气承包了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的1070亩荒地种粮。
有人说他,“你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!”
“正是,为啥我叫刘文豹呢?”
别人都说,“这些荒地根本就种不出来粮食,就算种出来,投入产出比也不划算。”但刘文豹从没想那么多,“在我眼里就没有种不好的地,我只想着怎么才能把地种好。”
“但是有些地确实不适合耕种啊?”
“地种不好,那是功夫没下到。”
就这样,他成了“中国农民规模经营第一人”。在历史潮流涌来的第一个浪头下,成为了弄潮人。不久后,刘文豹迎来了自己人生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如果说人这一辈子,活的是几个瞬间,那么1989年的那个正月,刘文豹永远也忘不了。他是在一个大雪天出发的,先是走了十几里的路到镇上,又搭了辆大卡车,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县里。在县里终于坐上了火车到了省城,再转车去北京。几天后,他终于踏进了中南海,与全国百名种粮大户一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,并获得了中国“一代粮王”的美誉。
种粮,是刘文豹最朴素的执念。以古驿镇为起点,40年来,从汉江上的襄阳鱼梁洲,到黄河边的宁夏银川和石嘴山,再到鄂北岗地上的湖北枣阳,在此期间,儿子刘斌、刘杰也加入种粮事业。目前,父子仨累计开荒改良土地2万多亩,生产7800多万斤粮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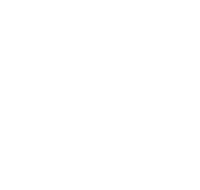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,刘文豹举家回到襄阳,在枣阳流转了2000亩土地种粮。父子3人又开始新一轮创业。
落户枣阳,刘文豹认为,这里基础好,对种粮大户也“高看一眼”。

其实,对刘文豹父子来说,20多年没有回湖北种粮,气候环境和种植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,面临的挑战也不少。第一年按照在宁夏的方式种了120亩水稻,因为温度高没撤水,三成没出苗,第二年灌完水以后就开沟,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。目前小麦、水稻、高粱、春玉米等作物的产量都高于当地平均水平,效益也很可观。
“这是赔出来的经验。”刘斌笑着说,去年收小麦的时候遭遇了烂场雨,雇了5台收割机,花了5天时间把1700亩小麦全部割完了,但是收购企业每天只能给我们烘干30吨,来不及烘干的被“捂”着发酵了,也没卖上价。
今年,刘文豹父子下决心跟镇上申请了一块农业设施用地,投资200万元建了仓库和两套烘干设施。对于年产粮食近300万斤的刘氏父子来说,有了这些烘干设备,每年能省下十几万元的人工费用。
而这笔精打细算的“长期投资”也寄托着刘文豹父子要在这里扎下根的心愿。

现在,刘文豹有两个“家”,一个家在襄阳城里,却只有每年过年走亲访友,才会回去住上几天;另一个家就在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的家庭农场,他和老伴、两个儿子就住在3间平房里。这里有他们的全部“家当”——两台大型收割机、7台拖拉机,还有新购置的烘干设备。
“乡亲们都愿意把地流转给刘文豹。他们看得出来,刘文豹对庄稼有感情。”董楼村党支部书记梅开军说,2023年,董楼村被纳入小田并大田试点,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村民大会,为刘文豹调整了270亩稻田,使他的稻田由200亩扩大到470亩。
梅开军告诉记者,他们把农户抛荒的田地集中流转给刘文豹。通过整合集并农村土地经营权,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,推动农田“优质、集中、连片”,进一步提升农业规模化、现代化经营水平,董楼村实现了农民、村集体双增收目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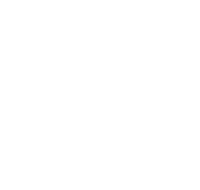
垦荒40年,终于种上了良田,刘文豹很知足。如今,刘文豹“退居二线”,担任“顾问”,农场交由刘斌、刘杰打理。
忙碌了大半辈子,老刘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两个儿子不仅接了班,还配合默契。刘斌擅长管理,担任家庭农场理事长,市场行情、品种技术都能看得准;刘杰精通机械,无人机打药、大农机生产都不在话下。但两个儿子却说:“父亲的想法总是有前瞻性,自己只是学了皮毛,大事还得听他的。”

“80后”兄弟俩终于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化大农业前景,准备大展拳脚。在年轻一代看来,“多种地靠的是不变的初心,种好地靠的是好政策和农业科技。”
虽然是实行规模经营最早的一批人,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,可骨子里流淌的中国农民本分实在的性格特点,深刻影响着刘文豹:从没想过一口吃个胖子,适合自己能力范围内的,就是最好的。
正是这种性格特点让刘文豹又一次跟时代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。为了避免土地集中于少数大户手中,造成小农无地可种的情况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,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。从此,“适度”成为土地流转的核心理念。
“我们流转的地够种了,不能盲目扩规模,要考虑成本和承受力。现在只是麦收抢农时雇几台收割机,其余的自己都能完成。”刘斌盘算着。父亲的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两个儿子,老刘始终有一条底线,就是不能资不抵债,“到时候万一还不上了,就会破产。”
如今的农业高科技,让种地变得轻松了。无人机打药可以自动规划路线,一天就能作业七八百亩,有时晚上再加个班,一天千把亩就搞完了。以前用打药车的时候,顶多一天作业200亩,还常常重复施药。播种则用上了北斗精量点播机,亩均用种是人工播种的1/3,成本却才一块多钱。

“现在种粮条件在变好,基础设施更加完善,科技水平越来越高。”刘斌忆苦思甜,现在农场的生产经营水平提升了,收成一年比一年好,2023年收了近300万斤粮食,挣了30多万元,基本又投到了后续的生产中。
“看我胖的,就知道全部机械化了,每年最忙时也就是收麦子抢种水稻,能瘦十来斤,收完就胖回来了。”刘杰笑着说,“而且这些机械的投入产出比很高,几年就能回本。”
这都是老刘过去想都不敢想的,他决定放手交给儿子们干。因为老刘知道,未来一定还会超出他的想象。

从传统农业到机械化生产再向智慧农业转型,从取消农业税到实施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……两代人跨越40年,在刘斌看来,多种粮,靠的是不变的初心;种好粮,靠的是国家好政策和不断进步的科技。
谈及未来,刘斌、刘杰还想进一步扩大规模,准备到周边再承接点地块。同时,加快优质稻的试种和品牌建设,提升销售端的价值。
(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)
文/图:周红南 采访一部整合
编辑:董子川丨校对:吴芳
责编:沈明晶丨审核:龚莉





请输入验证码